奮進新征程 建功新時代·陝西“一號公路”通車五周年特別報道
編者按
再走陝西沿黃公路,欣賞綠意正濃的黃土高原,體味歷史悠久的黃河文化,記錄沿岸百姓的生活變遷。
今年是陝西沿黃公路正式通車5周年。2017年8月28日,歷時8年建設的陝西沿黃公路正式通車,全長828.5公裡。這是陝西省沿黃河西岸的一條南北向公路,被譽為陝西“一號公路”。
這條路,北起榆林市府谷縣牆頭村,南至渭南市華陰市華山腳下,連接了9條高速公路、13條國省干線公路和80條縣鄉公路﹔這條路,把榆林、延安、渭南的12個縣(區)72個鄉(鎮)1220個村“串”在一起,還“串”起了西岳華山、洽川濕地、司馬遷祠、壺口瀑布、乾坤灣、吳堡古城等50余處名勝古跡景點﹔這條路,承載著沿線220多萬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5年來,這條路如巨型畫筆,繪就了黃土地上的共富底色。
記者深入陝西沿黃公路沿線村庄,記錄5年來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改善、特色農業發展、生態環境治理、文旅融合的生動實踐,講述這裡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故事。
牆頭 奔頭
陝西沿黃公路0公裡處,榆林市府谷縣牆頭便民服務中心牆頭村。
萬裡黃河一入陝,便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大彎,猶如母親的臂膀,將牆頭村擁抱在懷中。
王清玉在這兒生活了61年。生性粗獷的他,雖對這片熱土充滿感情,但一直羞於表達。在他看來,“家鄉”二字太過文縐縐,“祖祖輩輩待著的地方”才最貼切。
位於黃土高原上的牆頭村不再是黃沙漫天、黃土滿地,眼前綠油油的水澆地一眼望不到頭。
8月2日,牆頭村村民王清玉開著三輪車去村北的海紅果種植基地轉了轉。佔地350畝的基地裡,青綠色的果子挂滿枝頭。王清玉說,再過一個月,果子就全紅了。
站在樹下,王清玉拽下一顆海紅果,在衣服上抹了抹便吃了起來。雖然動作和以前一樣,但口感、心境卻完全不同。就像他說的,原來的海紅果是“酸”的,而現在卻是“甜”的。
期盼
王清玉家有輛驢車,多少年了他也舍不得扔,寶貝似的放在偏房一角。新房子蓋好后,妻子嫌驢車佔地方,幾次想處理掉,都被他攔下了。為這事,夫妻倆沒少紅過臉。
王清玉是個念舊的人。對他來說,這輛驢車既是父輩們留下來的念想,也是陪著他討生活的“功臣”,說啥都不能扔。
20多年前,王清玉的父親把這輛驢車鄭重地交到他手上。“娃呀,這個家以后就靠你擔著了。”當時,三十大幾的王清玉已經成家,深知這輛驢車對一個家庭來說意味著什麼。
地處晉陝蒙交界處的牆頭村,原來到府谷縣城隻有兩條路。一條是一人多寬的土路,路上到處是大坑,趕著驢車到縣城得3個小時﹔一條是橫穿黃河的水路,要坐擺渡船先到對岸山西省河曲縣,再到保德縣,最后才能進府谷縣城。
肩負著養家糊口的重任,王清玉去府谷賣過西瓜,去內蒙古賣過蔬菜,去山西賣過海紅果……他常常是天不亮就趕著驢車在渡口排隊,快中午才能坐上船。有時實在排不上隊,他就咬咬牙,走土路去府谷縣城,要是路上稍有點耽擱,回來天就黑透了。
有一年夏天,雨多,黃河發大水,船過不去。唯一的土路也被雨水沖斷了。
也是在那一年,王清玉家的兩畝西瓜長得特別好,個頭大得一個人抱都有點吃勁。他原本想著瓜賣了能給幾個娃娃湊點學費,可是直到開學前,水也沒退,路也沒修好。眼看著熟了的西瓜開始爛掉,王清玉一個人默默地扛著锨,把那些瓜全埋了。
“可要把日子往好了過,再不敢叫娃娃們跟著吃苦咧。”這些年來,一遇到事,王清玉就想起爺爺過世前對父親說的話。為著這句話,父親沒黑沒明地干了一輩子。
再后來,父親也不在了,臨終前對他說的還是同樣的話。
其實,不是父輩們沒本事,而是這風沙刮、河水淌的小村子,交通實在太閉塞了。即使遇上個好年景,也不頂個啥。王清玉說,收成再好,沒有路,誰來買?往哪兒賣?
讓王清玉欣慰的是,隨著“村村通”的普及,那條土路變成了3米寬的水泥路。雖然比之前方便了不少,可他心裡還有個執念:村子能通一條更寬闊的公路就再好不過了。
這條路,啥時候能通?王清玉在盼,牆頭村的老百姓也在盼。
陝西沿黃公路0公裡處,王清玉指著界碑,介紹這條路給牆頭村帶來的巨大變化。
轉機
從春忙到冬,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著。王清玉心裡憋屈,見了誰都沒有多余的話。
他不光要操心自家的小日子,還得想著怎樣讓全村800多口人都能過上好日子。那時候,還是村黨支部書記的王清玉,肩上的擔子可不輕。
他想法多、思路活,卻總見不著成效。帶著村民種谷子,谷子賣不上價﹔接著改種黃米,黃米產量又不行﹔好不容易嫁接了百十畝海紅果樹,果子銷路卻成了問題。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王清玉差點把自己在村裡的那點兒威望折騰光了。
富日子好過,窮家難當。那幾年,村上開大會,底下連個人影都沒有。干部坐在前頭,你看我,我看你,個個一臉苦相。
“事干不到人前去,叫大家咋個信任你?”當了幾十年村干部的王清玉,盡管有點無奈,但他心裡提著的那口氣,始終沒放下。
“你說甚?要修路?”2009年的一天,聽到這個消息時,王清玉急得鞋都沒穿好,一口氣跑到了一公裡外的鄉政府大院。
“看,這是規劃,有咱牆頭呢。”鄉干部說。王清玉接過那幾頁薄薄的紙,隻掃了一眼,就一屁股蹲到地上,結結實實地哭了一回。
連著幾天,晚上睡覺時,王清玉都把復印的那幾頁紙壓在枕頭底下。“不怕你笑話,我做夢都能笑醒。”他說,打小在黃河邊長大,家裡老幾輩都吃過交通不便的虧,他太清楚這條路的“分量”了。
當年7月29日,一條沿著黃河西岸一路向南的路開工了!
這條路,就是陝西沿黃公路!
由於部分路段施工難度大,挖掘機隻能“趴”在陡峭的山崖上,用液壓破碎錘一點一點地“摳”路基。僅榆林段一期工程路基全線貫通,就用了四五年時間。
施工的那幾年,王清玉經常在現場從早守到晚。他說,哪怕遠遠地看上幾眼,聽一聽開山放炮炸石頭的聲音,心裡也覺得踏實。
陝西沿黃公路正式通車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王清玉記得特別清楚。
那一天,牆頭村敲鑼打鼓,鞭炮齊鳴,全村800多口人聚在一起,比過年都熱鬧。
那一天,王清玉一直咧著嘴笑,不時還扯開嗓子,吼上幾句自己編的小曲:“沿黃公路修到牆頭來,老百姓樂在眉梢喜心懷……”
就像歌詞裡唱的那樣,牆頭村的“春天”來了!
新生
“村子要發展,路是關鍵。”這句話,王清玉這兩年見人就說。
自打沿黃公路通車后,牆頭村的村民種啥都賺錢。就在前兩天,王清玉家剩下的一點兒西瓜也賣完了。一算賬,5畝瓜一共賣了6萬多元!這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不光他一家,牆頭村的老百姓日子都好過了。
每年7月底,西瓜地騰了后種上大白菜,白菜行間套種些紅薯和花生,剩下的地裡,再種點兒玉米,一點兒綹綹地也不浪費。王清玉粗粗地算了下:去年,大白菜畝產達到2萬斤,地頭價一斤6角多錢﹔密植玉米畝產3000多斤,客商上門收購一斤1元多錢﹔加上雜七雜八的收入,一戶村民年收入輕輕鬆鬆就能突破六位數。
讓人欣喜的遠不止這些。隨著黃河流域生態治理力度不斷加大,牆頭村的山坡上、公路邊都栽滿了樹,昔日漫天風沙的黃土高原呈現出勃勃生機。這幾年,政策、項目、資金不斷在牆頭村落地,原來干啥還有點畏畏縮縮的王清玉,終於有底氣帶著大家伙大干一場了。
改善村容村貌,調整產業結構,成立海紅果種植專業合作社……牆頭村的每一步,都踩在了點上,“走”得穩穩當當。
路通了,機遇也來了。作為主導產業的西瓜,在牆頭村有了自己專屬的“節日”。“連續辦了多年西瓜節,1000多畝瓜不出村就被搶光了。一到那幾天,村裡車多得停不下,光維持秩序的就有100多人。”8月20日,王清玉齜牙一笑,說話聲都高了。
名不見經傳的牆頭村火了!
販瓜販菜的來了,旅游觀光的來了,學習取經的也來了。王清玉把這些歸結為“新生”帶來的蝶變效應。他說:“咱這兒現在是省級重點農業園區,海紅果、瓜菜都是增收‘名片’,家家戶戶都有了好出路。”
生活好了,心情也好了。王清玉家的堂屋裡有一張去年春節的全家福。一家十來口人穿著簇新的唐裝,個個笑容燦爛。有時候,他會對著照片出神,看著看著,那些年吃過的苦、遭過的罪就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在腦海裡回蕩。
如今,那些肩挑、背扛、驢車拉的苦日子早已成了歷史。這個“雞鳴聞三省”的小村子,每天都在演繹著“牆內開花牆外香”的新故事。
王清玉說,現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有奔頭。(陝西農村報記者 賴雅芬 黃敏/文 王東宇/圖)
古渡 今渡
陝西沿黃公路267公裡處,榆林市吳堡縣岔上鎮拐上古渡。
黃河水沉穩地向前流淌,在岔上鎮丁家畔村迸發出驚人力量,形成壯麗奇觀——天下黃河第二磧。從這兒往上一公裡,就是拐上古渡口。
20多年來,四錘一直守在這兒。用他的話說,渡口、碼頭就是他的家。
守了半天,沒等來一單生意,船工四錘有些煩躁。
8月5日,午后,太陽明晃晃地照在頭頂,碼頭靜悄悄的。來回轉了幾圈,四錘熱得直冒汗。他走到淺灘處,抽下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扔進水裡擺了擺,往臉上抹了兩把。
日頭漸漸偏西,青翠的山梁慢慢投下暗影。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四錘直起腰,緊了緊腰包,想了想,又伸手蘸了些水,捋了捋頭發。“人得精神些。”他說,這些是他“開工”前的准備。
堅守
擺渡行船,靠的就是一雙手。57歲的四錘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手藝人。
黃河上有很多渡口,啥時候有的,有多少個,沒有幾個人說得清,四錘也不知道。世代生活在拐上渡口附近的丁家畔村,四錘隻知道,打他記事起,父親和父親的父親就像渡口所有的擺渡人一樣,長年累月跑碼頭,養活一家老小。
丁家畔村坐落在黃河岸邊的山窩窩裡,與山西省呂梁市臨縣磧口古鎮隔河相望。以前不通公路,從村裡到吳堡縣城隻有一條盤山土路,坑坑窪窪,一去一回一天就沒了。可從碼頭坐船到對岸的磧口古鎮隻要10分鐘。鎮上店鋪林立,賣物換錢、購物辦貨都很方便,一天能打十幾個來回。
守著古渡,守著碼頭,這個封閉的小山村多了一些希望。
在四錘的記憶裡,有一段時間,渡口跟菜市場一樣熱鬧。每天從早到晚,老老少少挑著擔子,趕著牲口,在碼頭上排隊上船。父親在船頭使勁劃著槳板。到了對岸,人們卸貨下船,父親汗津津的手上就多了幾張鈔票。
“這是咱吃飯的營生,好好經管。”父親老了,擺不動船了,就把祖父留下的木船給了四錘,囑咐他,“行船不光是賣力氣,也是手藝活,可不能丟了。”
四錘到現在都記得,那一天,父親坐在炕上,煙抽了一鍋又一鍋,同樣的話說了一遍又一遍。
這些年,除了刮風下雨,四錘幾乎天天都守在渡口,等客,渡客。“父親下了一輩子苦,到老都沒見過柴油渡船。”四錘說,自己比父輩幸運,趕上了好時代,還掌握了新手藝,柴油渡船、動力汽艇樣樣都能“擺”。
四錘其實是有大名的,叫李常平。只是擺渡的時候,大伙喜歡站在碼頭上叫他“四錘”。日子一天天過去,碼頭昔日的繁華如流水般一去不返,但守在渡口已經成了四錘雷打不動的習慣。
雖然有了柴油渡船、動力汽艇,但是一有空,四錘就會把木船拾掇拾掇,一直也沒舍得扔。他也說不清為啥,可能就像鄉親們說的,看到渡口,看到這船,就像看到了回家的路。
四錘“擺”著渡船,將一撥游客連車帶人送到了對岸。
破冰
在碼頭上討生活是件苦差事,風吹日晒不說,搖櫓撐船費人費力,遇到漲水起大浪還有危險。開始那幾年,拉一個人單趟才一元錢。四錘不挑客,一元錢都要掙到手。就這,他的日子還是過得緊緊巴巴。
咋樣才能把日子過到人前頭,讓娃娃們走出窮山溝?這個問題,一直在四錘腦子裡打轉。
那時候,山上不通路,溝溝坎坎都是黃土,想找條出路談何容易?四錘咬牙撐了兩年。木船該翻修了,他一打聽,得一萬多元,快抵上動力船的價格了。四錘覺得不劃算,跟妻子商量了幾宿,一咬牙就置辦了一艘柴油渡船。
承載著祖父和父親兩代人記憶的舊木船,從此“功成身退”,被擱在了岸邊。
柴油渡船不費人,載重可達三四噸,拉車拉人都很輕鬆。盡管如此,可碼頭上擺渡謀生的不止四錘一個人,他的日子還是很難。
如果沒有修路,生活可能就這麼平淡無奇地過下去了。四錘做夢都沒想到,丁家畔村幾代人盼了幾輩子的水泥路,真的通到了家門口。緊跟著,農村公交也有了。再后來,村裡的棗啊、糧啊、牲口啊都有了“出路”,再也不用搶著“過河”了。
不知道從哪天開始,碼頭上擺渡的人少了,坐船的人也少了,有時幾天都等不到一單生意。四錘知道,世事變了,變得更好了,他既高興,又失落。
半輩子沒出過山,不擺渡能干啥?那段時間,四錘黑天白日都在尋思著,經常一個人在空蕩蕩的碼頭一坐就是一天。
“船停在碼頭壞不了,有人了掙個零花錢,沒人了就務庄稼,照樣能過。”四錘這樣安慰自己。
真正的改變在2017年。那年秋天,山上的大棗快紅透時,鄉親們成天念叨的沿黃公路正式建成通車。這條路,更長、更寬,沿著黃河西岸,從丁家畔村和拐上古渡間一穿而過。
路通了,丁家畔村通往外界的“窗口”更大了。站在渡口,看著南來北往的車輛,四錘又一次覺得,生活更有奔頭了。
那年冬天特別冷,黃河上結了一層薄冰,古渡越發冷清。四錘卻整天樂呵呵的。他想著,轉過年,春暖花開,河面的冰化了,這兒的光景就不一樣了。
出圈
道路通,百業興。
四錘深刻地感受到,這條寬闊的沿黃公路給村子帶來的改變不是一星半點。自從路通了,丁家畔村也變了模樣:村子美了,產業旺了,原來賣不上價的農產品一下子成了搶手貨,家家戶戶蓋新房、買汽車,日子一天比一天紅火。
黃土高原的溝溝峁峁也在不經意間都披上了“綠裝”,黃河邊路成網、樹成林,一年到頭都是綠油油的。
“以前到處都是黃土梁梁,風一吹,喉嚨裡都是土。”四錘沒去過江南,在他的心裡,現在的黃河沿岸山清水秀,跟江南一樣美。
四錘家的5孔窯洞就建在沿黃公路的邊上,離渡口也不遠。
如今,沿黃公路成了遠近聞名的觀光路。吳堡縣借力打造拐上古渡濕地公園,推動特色產業、生態文化和鄉村旅游融合發展。古渡、碼頭、黃河灘,有游客說,這裡有滿滿的鄉愁。
四錘不懂啥叫鄉愁,他依然堅持守著渡口。有人過河,他就扔下手上的活,連車帶人送到對岸去,一趟下來能掙五六十元,比以前多了好幾倍。
“用錢的地方還多著哩,我多掙些,娃娃們就少受些苦。”腰包鼓了,一雙兒女走出了丁家畔,這是四錘最驕傲的事。
這兩年,渡口人氣又旺了起來。過河,漂流,干啥的都有,上門的營生咋能錯過?不顧妻子反對,四錘從城裡買回了一艘汽艇,練了幾天就上手了。
“不管啥船,道理是一樣的。”四錘對自己的“手藝”很自信。今年過年,趁著娃娃們回家,他還學會了抖音直播,專門介紹黃河以及拐上古渡的好風光。
開播沒多久,四錘就收獲了一批“粉絲”。他感到很新奇,於是得空就拿著手機東晃西晃。“黃河出圈了,古渡也快了。”說這話的時候,四錘的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太陽落下了山頭,一輛接一輛的小汽車駛進了渡口。看到生意上門,四錘的眉頭展開了。一番討價還價后,他解開鐵索,跳上渡船,發動馬達,對岸越來越近。這單生意,成了!(陝西農村報記者 黃敏 賴雅芬/文 王東宇/圖)
小院 小康
陝西沿黃公路479公裡+800米處,延安市延川縣乾坤灣鎮龍耳則村。
村子東北大約10公裡外,就是“天下黃河第一灣”——乾坤灣。在這裡,母親河就像一條巨龍,在黃土高原的溝壑間奔騰不息。
圍著鍋台轉了大半輩子,55歲的馬彩梅一直守著自家的那個小院子,縫縫補補,洗洗涮涮。沒出過遠門的她,不止一次地憧憬過外面的世界。
龍耳則村村民馬彩梅家的5孔窯洞朝南一字排開,間間寬敞明亮。鋪著藍花花床單的大炕中間,擺著一個四方小炕桌。再往裡,幾床被子疊得像豆腐塊一樣,方方正正。
就這,馬彩梅還覺得不夠整潔。拿著掃炕笤帚,她又一下一下仔仔細細地把炕上的床單掃得看不見一個褶兒。
馬彩梅是個麻利人,每天一睜眼,就要把窯裡院裡拾掇一遍。她說:“收拾干淨了,客人住著才舒服。”沒念過書的馬彩梅不懂啥大道理,隻知道一點,要讓住到自家窯洞的人有回家的感覺。
作為村裡現在的5家民宿之一,馬彩梅家的窯洞是檔次最高、生意最好的。8月9日,說起自家的生意,馬彩梅表示,別看現在日子紅紅火火,可她和丈夫背地裡吃的苦,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困惑
馬彩梅的丈夫呂金福家裡弟兄多、拖累大,光景過得一般。當初,馬彩梅就是圖著呂金福為人踏實、知根知底,才啥都沒要就跟了他。
延川縣紅色資源豐富,自然景觀壯美。離馬彩梅家不遠的地方就有好幾個旅游景點。當初嫁過來的時候,馬彩梅就盤算著,隻要兩個人舍得力氣不怕苦,日子指定差不到哪兒去。可她沒想到,他們會在這山窩窩裡一扑騰就是好些年。
剛結婚的頭幾年,馬彩梅兩口子住在龍耳則老村溝底下的一孔爛窯洞裡。雖然條件不好,可馬彩梅從沒埋怨過,她跟丈夫有商有量地經營著自己的小家。
“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既然成了一家人,就要相信他。”馬彩梅知道,丈夫不是那種“破罐子破摔”的人。光景過不前去,丈夫雖然嘴上不說,但心裡也像貓抓一樣,急得很。
后來,村裡條件好一點的人家陸續都搬到溝上面的平地上去了。馬彩梅兩口子還是守著幾畝山地,一天一天地、一镢頭一镢頭地“刨”生活。盡管頓頓清湯寡水,可他們堅信:眼下的苦,是暫時的,生活的甜,在后頭呢。
山裡人干活,離不了牲口。每年開春,馬彩梅都會翻出壓在箱底的紅手帕。那裡頭,裹著頭一年好不容易攢下的一點兒“家當”。她一張一張數上好幾遍后,小心翼翼地讓丈夫裝進貼身衣服的口袋,最后再用別針把開口處別緊。
從集市上,呂金福牽回一頭毛色光亮、高大健壯的騾子。可是沒養多久,騾子就莫名其妙地死了。連著幾年,年年如此。馬彩梅說,人倒霉了,喝涼水都塞牙縫。呂金福卻說,這是把牲口使得太扎實,加上不會喂養,才出的問題。
靠山靠不住,種地產不出,一年忙到頭,手裡也沒有幾個錢。眼瞅著娃娃一天天長大,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再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馬彩梅兩口子籌謀了幾天,也沒想出一個掙錢的好門路。
馬彩梅心裡有困惑,也有不甘。
馬彩梅在家門口的小花園裡忙活。
謀變
苦歸苦,難歸難,可馬彩梅和丈夫的心勁一點兒都沒減。在這片紅色熱土上,最不缺的就是艱苦奮斗的精神。
兩口子朴實,啥苦都能吃。村裡沒人種的綹綹地,山上長滿草的台台地,他們都鋤得光淨光淨的,種上了庄稼,栽上了棗樹。干,總比不干強。他們心裡清楚,在沒有找到更好的營生前,種地是唯一的指望。
就這樣,省吃儉用了好幾年,一家人硬是從牙縫中一點一點“摳”出了一些閑錢。可要箍起幾孔窯洞,這點兒錢遠遠不夠。咋辦?
再難,日子總要往好了過。一狠心,呂金福撇下妻兒老小,一個人跑到外頭打工去了。
搬石頭、扛貨物、攬零活……呂金福不怕苦,別人嫌活重錢少不願意去,他二話不說就接過手。“慢慢干著,慢慢攢著,總有攢夠的一天。”呂金福說。
抱著這種想法,兩口子一個在外下苦掙錢,一個在家種地管娃。幾年下來,總算把箍窯洞的錢攢夠了。
龍耳則村的人箍窯洞,都要到老村的溝底下拉石頭。別人一天拉四五趟就是多的,可呂金福非要拉八九趟不可。
對馬彩梅來說,丈夫就是她的天。她心疼自家男人,不想讓他太累。有一次,跑完第八趟的時候,騾子累得臥在地上,呼哧呼哧喘著粗氣,咋拉都拉不起來。呂金福也受傷了,小腿被石頭砸破,血直往外冒。就這,他還掙扎著要再拉一趟。
“人重要還是窯重要?照你這弄法,窯還沒箍好,你就被撂倒了。”從來不大聲說話的馬彩梅,頭一次吼了丈夫兩句。過后,她又有點自責,晚上吃飯時,悄悄給丈夫的碗裡多臥了兩個荷包蛋。
窯洞箍好的那天,是個大晴天。站在亮堂堂的窯裡,馬彩梅笑著笑著,眼淚就流了下來。呂金福搶過妻子手裡的笤帚,把新家從裡到外打掃了一遍。
兩口子憋了半輩子的勁兒,在這一刻釋放了。
逐夢
馬彩梅愛干淨,丈夫呂金福則不太講究,他還嫌妻子“事兒多”。在一塊過了幾十年,馬彩梅一直想讓丈夫跟自己一樣干淨利落,可每次一提這事,兩人就要打一場嘴仗。
但這兩年,呂金福變了。他不光收拾自己,有時還幫著馬彩梅把屋裡拾掇一下。馬彩梅打趣地說:“哎呀,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呂金福總是嘿嘿一笑說:“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可不能給咱掉鏈子。”
現在,的確和以前不一樣了。馬彩梅的新家緊挨著沿黃公路。通車的前兩年,就有村干部在他們耳朵邊“吹風”:“把窯洞改成民宿,城裡人沒住過,稀罕得很。沿黃公路通了,來的人肯定少不了。”
事是好事,可馬彩梅心裡有點打鼓。她不善言談,不知道咋和外人打交道。丈夫安慰她:“你就當和村裡那些婆姨拉話,說錯了也沒人怪你。”馬彩梅這才覺得自己好像有那麼點底氣了。
開民宿,3孔窯洞肯定不夠。兩口子一尋思,拿出多年積蓄,又在旁邊續了2孔。每一孔窯洞都配了衛生間,裝了馬桶和淋浴器。馬彩梅還“攛掇”著丈夫把原來開在西邊的大門改到了正南方向,又在門口撒了些格桑花種子。
“門朝南,向陽,人來了一眼就能瞅見。”說這話時,馬彩梅眼裡閃著光。
2017年8月28日,沿黃公路通車。那一天,馬彩梅家門口的格桑花開得正艷。紅的,黃的,粉的,一大片花兒迎風輕擺。
那一年的國慶節,來乾坤灣旅游的人一撥接著一撥。馬彩梅家的5孔窯洞,住得滿滿當當,半個村的人都跑到她家看稀奇。
第一天面對客人,馬彩梅緊張得說話都有點結巴。可沒過幾天,她就能操著一口不太熟練的普通話向客人推薦自己的拿手菜了。
白天洗菜做飯、張羅吃喝,晚上打掃衛生,准備第二天的食材。那段時間,馬彩梅一天隻睡三四個小時。可她一點兒也不覺得累。“咱這是追求自己的好日子呢,再累心裡都是歡喜的。”馬彩梅說,那個假期,她掙了一萬多元。這個圍著鍋台轉了半輩子的婆姨第一次體會到了掙“快錢”的興奮感。
假期一過,游客少了,馬彩梅兩口子還是閑不下來。除了民宿,家裡還有40多畝葡萄園,正是賣錢的時候,得悉心經管。
現在,不忙的時候,馬彩梅就愛坐在院中間的石凳上往遠處瞅。
天藍、地綠、水清……馬彩梅說,這美景咋都看不夠。這不就是自己以前向往的生活嗎?(陝西農村報記者 賴雅芬 黃敏/文 王東宇/圖)
老村 老腔
陝西沿黃公路828公裡處,渭南市華陰市岳廟街道雙泉村。
千百年來,黃河水浩浩湯湯,滋養著兩岸的百姓,催生出許多古老而燦爛的文化。華陰老腔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華陰老腔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75歲的張喜民最得意的就是和老腔一起登上了世界舞台。這是他的榮耀,也是華陰老腔的高光時刻。
“八百裡秦川,千萬裡江山,鄉情唱不盡,故事說不完,扯開了嗓子,華陰老腔要一聲喊……”8月12日,早飯后,雙泉村村民張喜民像往常一樣拉著孫子張猛在院裡的葡萄樹下練“吼功”。爺孫倆,一個抱著月琴,一個拿著板胡,一彈一拉間,一聲聲“吶喊”令人震撼。
陽光很好,密匝匝的葡萄藤蔓在院子裡遮出一片清涼。唱了一陣,張喜民覺得不過癮,又聊起了老腔的“前世今生”。盡管聽了無數遍,張猛還是聽得很認真。
積澱
雙泉村是個有故事的地方。
2000多年前,黃河上的漕運船工為統一動作,一邊用木塊敲擊船幫,一邊喊著號子。這是老腔的雛形。此后,居住在村裡的張氏族人,將號子記在心間、唱在口中,並與后來的皮影戲結合,形成獨特的“家傳戲”,一代代口口相傳。
關於老腔的這段歷史,張喜民從小聽到大。家裡有個說不上年代的戲箱子,裡頭放著50多本發黃的老腔劇本,寫的大都是些老故事。
“父親在世時把這些老腔劇本當寶貝,看得比命都重,東藏西藏,就害怕叫人偷了。”在張喜民心裡,這既是祖輩傳下來的“家當”,也是張家人吃飯的“家伙”,丟了,就等於砸了飯碗。
2000年以前,老腔和皮影戲從沒有分開過。那時候,人們看戲,隻能看到白幕上的幾個影子。幕后,操作皮影的簽手一邊表演,一邊彈樂器,時不時仰頭吼上幾句。
“台下的人光能看到幕布上的皮影在動,角色自如轉換,他們不知道,幕后可能隻有兩三個人在表演,每人拿幾把樂器,同時演幾個角色。”張喜民從小跟著父親唱老腔、學皮影戲,15歲時就正式開始表演了。
世代生活在這兒,張喜民對這片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風土人情再熟悉不過了。用他的話說,老腔、皮影戲滿是“黃土味”,演的不光是黃河的歷史,也是自己的生活。
剛開始那幾年,張喜民一年能演上百場。“誰家過紅白喜事,不演幾場皮影戲,鄉黨那裡都說不過去。”經常走東家、串西家,張喜民越來越覺得,老腔不能總是老一套,得出新戲、唱新詞。他說:“任何文化形式,隻有跟上時代才能長長久久地走下去。”
閑下來,張喜民就把老劇本翻出來,照著老段子、老曲子編詞改戲。這一改,還真有效果。后來幾年,“請戲”的人越來越多,老腔也在一天天的“積累”中更有看頭。
聚力
大概是2000年的冬天,張喜民帶著班子去鄰村表演。台上,皮影戲人物短兵相接,戲唱得鏗鏘有力﹔台后,他和幾個老伙計趁著空兒喝壺茶、咥碗面。放下茶杯、碗筷,大家繼續吹拉彈唱,忘情投入。
這一幕剛好被當時在華陰市文化局工作的黨安華看到。戲剛演完,他就找上張喜民。
“人影比皮影還精彩,要是把幕后場景搬到台前,肯定更吸引人。”黨安華的話,張喜民一直都記著。
老腔自打出現后,都是幕后表演、台前看戲,現在要讓自己登台亮相,張喜民實在沒有底氣。他說:“沒有了皮影戲,老腔唱啥?塌火了咋辦?”
后來,黨安華幾次上門勸說,張喜民決定試一試。沒抱什麼希望的他,咋都沒想到,離開了皮影戲的老腔會火得“一塌糊涂”。
“伙計們,准備好了麼?”
“好咧!”
“抄家伙,曳一板。”
……
排練了十來天,第一次在專家面前露臉,張喜民手心全是汗。他說:“太緊張了,腿抖得就沒停。”
短短10分鐘的表演,張喜民覺得好像過了一個世紀。台下的人,他一個都沒看清,兩眼一閉全身心投入演出。
表演結束了,台下掌聲雷動,張喜民一邊笑著,一邊流著眼淚。那一次,他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喜極而泣。
“邁出這一步,太不容易了。”張喜民回憶,以前的雙泉村交通落后,沒啥產業,老百姓一年四季除了務兩料庄稼,沒有多少事,看皮影戲、聽老腔成了打發農閑的主要消遣。老腔紅火的時間就那麼幾年,再后來,娛樂活動越來越多,“請戲”的人就少了。
張喜民也曾急得滿嘴起泡,能用的法子用遍了,還是沒有起色。他原以為,這樣下去,老腔的處境會越來越難,卻沒想到,處在低谷的老腔,竟然絕處逢生,一下子“躥”到了台前。老腔又紅火了。
此后,張喜民和村裡的老腔藝人開始了和以往不一樣的表演。老腔,慢慢地“走”出了這個古老的村落,一步一步,積聚著力量。
2006年,華陰老腔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張喜民(右)教孫子張猛彈唱華陰老腔。
傳承
老腔過去是“家傳戲”,很長一段時間裡“隻傳男不傳女”,其他人想學更是沒有門路,加上以前交通不便利,村裡的人走不出去,外面的人進不來,導致老腔隻能在華陰一帶“小打小鬧”。
從幕后到台前,老腔“走”了太久。而要想上“大場子”,老一套肯定不行。那時候,沿黃公路快修到村口了,雙泉村也開始著手調整產業結構,像老腔這樣的傳統文化與產業、生態多元融合已成了發展趨勢。黨安華提議大家組成“正規軍”,他來幫著編劇本、聯系演出,讓老腔能夠“走”出華陰、“走”向全國。那時候,黨安華也沒想到,自己看得還是不夠遠。
接下來幾年,一伙人唱遍了全國,也去過國外。短短幾年,老腔“走”出了華陰,“吼”向了世界。
“土戲”為啥能火?張喜民想了好長時間,才琢磨出些門道:“老腔的‘吼’,就跟黃河的‘吼’一樣,是一種精神,一種黃河邊老百姓為過上安生日子而奮斗的精神,咋能不吸引人?”
2016年,老腔又火了一把。央視春晚的舞台上,一群帶著土氣的老藝人用粗獷的吼聲驚艷了億萬觀眾。
“年沒過完,就有人跑來拜師。”張喜民興奮地說,“老腔要火下去,沒有傳承人咋行?有人願意學,我巴不得呢。”
老腔在變,老村也在變。這些年,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一棒接著一棒干”,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越來越好,雙泉村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沿黃公路的開通,更是把村民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資源“送”進了村。老村變美了,出行便利了,游客進來了,到雙泉村聽原汁原味的老腔成了“熱點”。
路通了,老腔的“出路”也多了。可張喜民卻為老腔后繼無人發愁。他說,這幾年,村裡人人都會唱幾句,但真正學的卻沒有幾個,不是年紀大,就是沒天賦,來拜師的也是湊熱鬧的多,挑來挑去也挑不出好苗子。
“滿打滿算,華陰會唱老腔的才20多個人,還都是些半大老漢。有人看,沒人演,不頂啥。”張喜民說,幾年前,他把孫子張猛當成接班人,從調琴到唱功,從編詞到說戲,手把手地教。幾年下來,張猛唱得有模有樣,還跟著張喜民上過幾次“大場子”。
“爺,再整一段?”
“整就整!”
小院裡,爺孫倆聊著聊著,又吼上了。“婆姨漢子耕黃土,千載悠悠唱老腔……”看著眼前年輕的面孔,張喜民抱著月琴彈得越發起勁。
老村的故事還在繼續,老腔的“吼聲”還在回蕩。(陝西農村報記者 黃敏 賴雅芬/文 王東宇/圖)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熱門排行
- 1陝西省部分高校調整開學返校時間
- 2西安新增12個高風險區10個中風險區
- 3西安市新增2個中風險區
- 4秦嶺大熊貓“秦秦”再次產下雙胞胎,…
- 5西安東站及相關工程獲批 計劃年內開工
- 6西安新增4個高風險區5個中風險區
- 7陝西省多地多部門全力以赴應對持續旱情
- 8陝西:綠色稅收描繪綠水青山新畫卷
- 9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組進駐…
- 10陝西電力累計向四川送電15.5億千…
- 11陝西寶雞:西山裡的旅游發展路
- 12我國首個風投驅動商業聚變探索裝置落…
- 13西安1個高風險區5個中風險區降級
- 14陝西:嚴防嚴控“防輸入”
- 15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兩手都要抓、都要…
- 16防疫一線當先鋒 志願服務展風採
- 17陝西“四個轉變”優化執法方式 讓生…
- 18國家稅務總局西咸新區灃東新城稅務局…
- 19科學精准防控 嚴防疫情通過鐵路傳播
- 20要求認真組織學習《習近平強軍思想學…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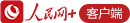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