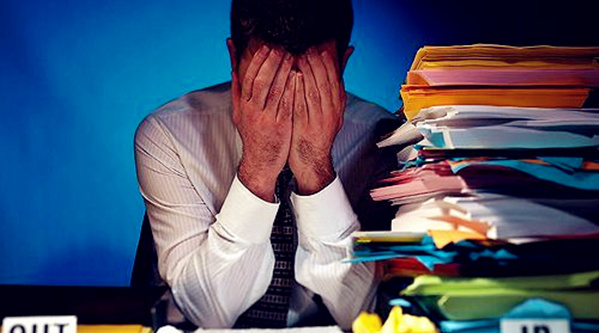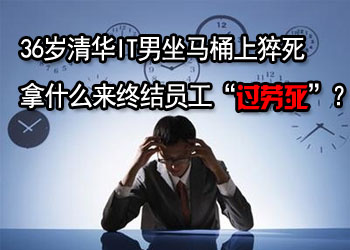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来自网络
 你是加班还是被加班?
你是加班还是被加班?
据了解,这位36岁的IT男(张斌)生前负责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死前一天还跟母亲说“我太累了”。不仅是张斌的妻子认为,而且有张斌的同事证实,他们长期加班的情况的确存在,从这样的证人证言中不难得出结论,张斌是一个“过劳死”的悲剧。
过劳死”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一项涵盖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和沈阳等7个城市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这决不是“矫情”,现实中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倒下甚至离去的,并不在少数。
 过劳死现象为何在身边大量存在?
过劳死现象为何在身边大量存在?
调查表明:不少上班族都表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加班是家常便饭。从表面看,有时是单位要求加班,有时是自己主动加班。其实很多主动加班,也是不正常的劳动关系的反映。许多用人单位崇尚“加班文化”,故意在单位制造紧张压力,不加班的很难得到上升机会,甚至连位置都保不住。于是也就出现了,加班压力大,不加班压力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几声道德谴责和呼吁,很难改变“过劳死”现象。【详细】
 “过劳死”已成生命隐形杀手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过劳死”已成生命隐形杀手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36岁清华IT男猝死,一句“我太累了”,道出了过劳死的心酸。近些年来,过劳死的新闻频频出现于各大媒体,据统计,我国每年心脏猝死的总人数高达50万人;目前,我国大城市白领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这是很可怕的社会现象,让和谐社会伤不起。
究其原因就在于竞争压力导致人才被透支使用。
中国正在向城市化和社会化过渡,转型期间,各种竞争压力急骤增加,为了保持社会的高速发展,不少紧缺人才被透支使用,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健康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更有不少企业,将员工是否经常忘我地加班劳动作为考核参考项,那些“不辞劳苦”、“废寝忘食”的员工经常被当作典范加以鼓励和赞赏,反之则多少会被认为没有将工作放在第一位,而遭遇领导的冷眼。而这些境遇,在知识层次高、竞争压力大的白领阶层也已司空见惯。
【详细】
 从IT男过劳死看出法律缺位之觞
从IT男过劳死看出法律缺位之觞
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对“过劳死”的法律规制仍然贫瘠与缺位,众多“过劳死”事件的处理结果,用人单位都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若出于人道主义给予死亡员工家属一定补偿,已然可以称为“善”后。在如今倡导以人为本的中国社会,为何能容忍员工以如此残酷的方式“自愿”加班劳累至死?
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劳动法律法规仅对加班薪酬、工作时间进行了规范,都未对“过劳死”作出规定。而因“过劳死”法律规制的缺位,受害劳动者得不到法律救济。
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过劳死”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模糊,但对于主观要件的认定,即是否应当以用人单位的有无主观过错来定义“过劳死”,是争议焦点。
但“过劳死”并不能全赖用人单位的主观过错,而应将之放在现代化大生产的背景之下,“过劳死”如何成为一种异化的社会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过劳死”往往发生在员工“自愿加班”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一种以指挥和服从为特征的管理关系。用人单位通过因势利导,将加班和绩效考核挂钩,使得“员工自愿加班”成为对“企业安排加班”严格监管的规避方法。
所以“过劳死”的认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还有赖于医疗事业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及相关的配套制度。【详细】
 首先要正视“过劳死”现象
首先要正视“过劳死”现象
一是从法律层面上对劳动者加以保障。一方面应加大劳动法的宣传及贯彻实施力度,教育引导决策者与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树立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健康发展理念,保持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尽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考虑“过劳死”这一特殊的职业病的防护与维权。
二是工会组织要创造性地开展关爱及维权工作。如针对处于“过劳”状态的白领群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不妨把柔性维权作为工会的一项时尚工作,开展各具特色的“减负”活动,通过职工疗休养、文体活动、心理按摩等渠道,为业务骨干、职工群众开出一张张预防“过劳”的良方。
三是职工本人要珍爱自己的生命健康。作为职场人,可忙里偷闲地去放松调节自己,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如听音乐、练书法等;坚持体育锻炼,如跑步、拉单杠和打篮球等;夫妻之间、朋友之间聊天倾诉,避免在心中郁结压力和不快的情绪。
【详细】
 其次对“过劳死”不能止步于个体反思
其次对“过劳死”不能止步于个体反思
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包括所有的死者在内,其实绝大部分人都面临着不得不处于那样一种潜在“危险”的困境之中。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物质的繁荣时,也直接将所有人导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状态。尤其是在“任劳任怨”“勤劳致富”等传统观念影响下,因竞争而忽视身体的隐疾,更成为一种不自知的常态。也正因为此,当我们谈论过劳死时,其实很少着眼于公共层面,而往往更多是止步于个人生活习性的反思上。
有必要提醒的是,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与行业大转型的当下,社会与行业的变迁传导到个体身上,就将引发更大的过劳压力和精神上的焦虑。因此,呼吁强化对于过劳死的公共干预已经刻不容缓。
不可否认,“过劳死”的出现有着很强的社会属性,包括社会的劳动文化、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等,可以说是诸多发展问题在人身上的“化学”反应。因而它的缓解与避免很难说能够通过某种措施达到立竿见影之效,但作为一种已经看得见的“威胁”,公共层面的重视,却必须加速。不能对普遍性的死亡危机无动于衷,这应该是一个人本社会所必须兑现的公共底线。【详细】
 过劳死预警机制刻不容缓
过劳死预警机制刻不容缓
面对日益增加的过劳死,员工不能总是成为孤独无助的沉默者,过劳死预警机制以及更深入的法律监管体系,已经到了制定时间表的关键时刻。包括过劳标准的确立、拓展员工对抗企业制定不合理规定的权利伸张空间以及事后对于违法企业的严厉惩戒,都需要在法律中落地。【详细】
但愿清华硕士张斌之死,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过劳死”是可耻的悲情,它牵扯着有相关部门对国民健康的制度保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等,也呼唤政府对公众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给予更高层次的关注。【详细】
要想终结“过劳死”,首先要正视它是一种异化的社会现象,若想破解这样的“异化”,就不能让“过劳死”止步于个体反思,必须强化对过劳死的公共干预,特别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多管齐下,有的放矢。相信终有一日“过劳死”会离大众工作生活越来越远。
 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来自网络 你是加班还是被加班?
你是加班还是被加班?
 过劳死现象为何在身边大量存在?
过劳死现象为何在身边大量存在?